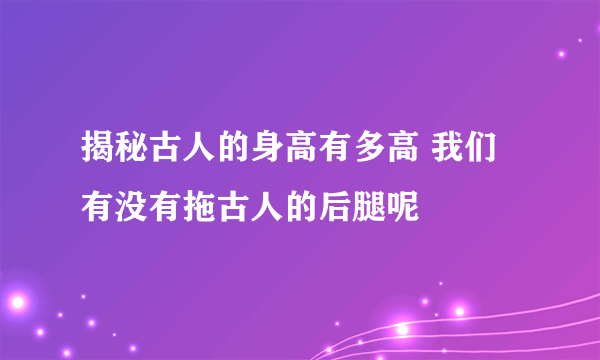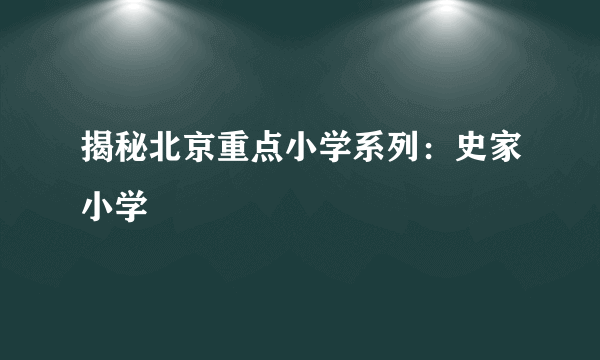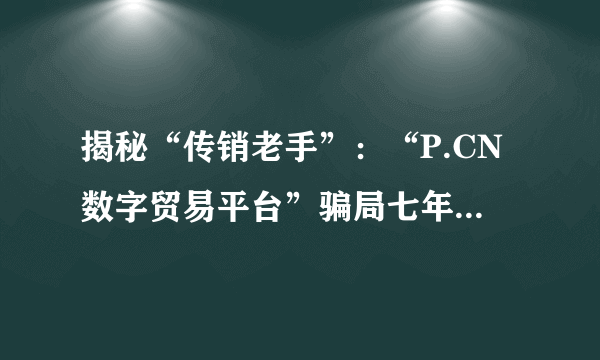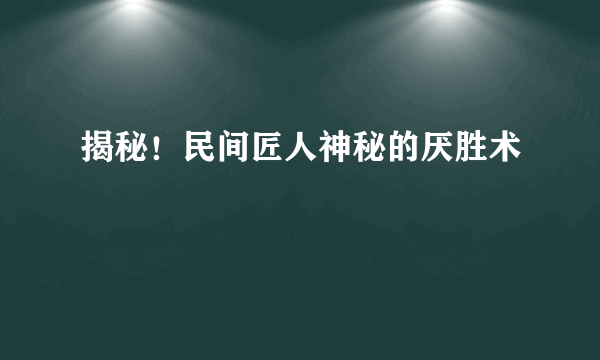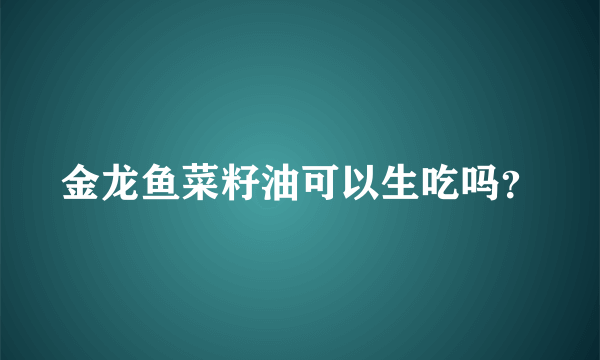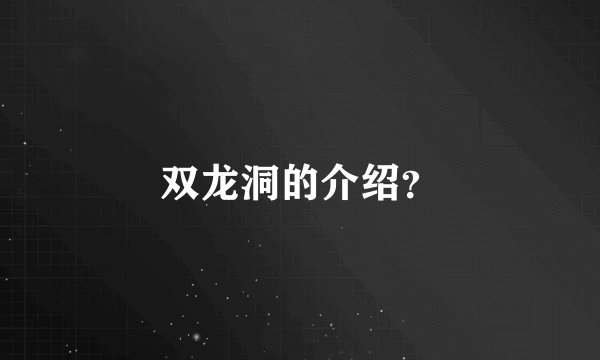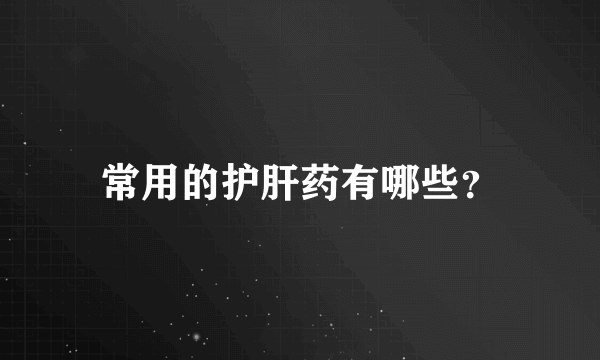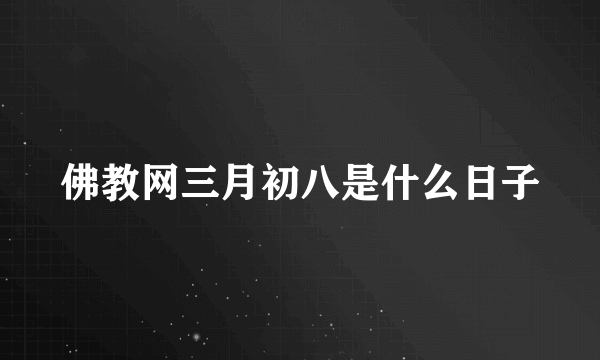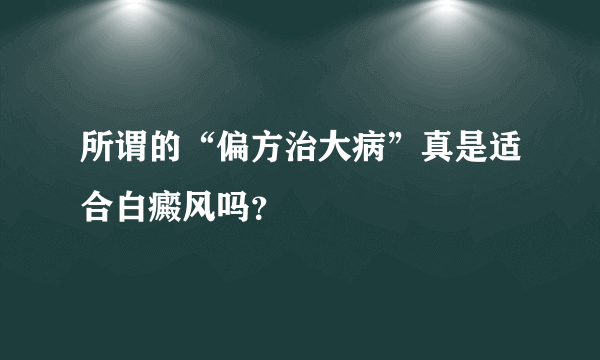出租屋旁群体吸毒
这些天来,经过多管齐下的断然措施,广州火车站广场这个曾被市民目为一大“毒瘤”的地区,开始出现治安秩序向好的端倪。
然而,我们发现许多熟门熟路在车站广嘲混混”的作案人员,出没的地方固然是在火车站广场,但是,令他们得以“落地生根”的土壤,却是在车站广场附近的“都市村庄”。于是,从6月3日起,我们的五名记者郑杰、李宜航、赵世龙、邓勃、王宁德,乔装暗访,涉险犯难,分头住进了新市、三元里一带的出租屋。
记者在里面生活了整整七天。艰苦的明察暗访,不仅使他们在火车站广场的“左邻右舍”看到现代都市竟有如此狰狞的社会生活角落,也透视出城市管理微观领域的许多弊端。我们认为,有必要将他们的所见所闻,分批公诸报端,以振聋发聩;也认为有理由大声疾呼:整治火车站必须同时整治周遭的出租屋!
应声开门:一张女人的脸!
嘘!
有人敲门。
进来的不是治安队员,是一张女人的脸。
我们住在三元里村的世康大街7号,本月3日入祝此时,是4日晚7时,夜幕刚刚拉上。
“我是你们对门邻居,‘士多’的阿芹。”女人显得很大方。
阿芹主动扯开了:“我以前开发廊,现在风声紧,不开了。哦,现在开发廊的都转移到‘士多’了。‘士多’安全,别人不会怀疑,说起来也好听。我手下有六七个小姐,个个都很靓。有个××省的,那皮肤……我见你们住进来,邻居嘛,关照你们一下。”
“关照什么?”
“睡觉呗。等着啊,我现在就去帮你们叫,包管满意。”
没等我们反应过来,阿芹已经走了。两分钟工夫,阿芹就领来一个姑娘,颇有几分姿色。
姑娘自称小倩,21岁,梅州人,6岁随父迁到外省,前年来广州“捞世界”。她先在发廊做,后来发廊关门,就被“妈咪”阿芹养起来。阿芹给她租了一间房子,就在三元里世康大街。阿芹在“士多”帮她物色男人,赚的钱两人分。一般收“客人”130元,小倩得100元,阿芹得30元,交10元保护费。三元里离火车站近,很多白天在火车站炒票的、摆摊的、贩毒的、吸毒的,晚上都来这里买欢,出价也不低,小倩目前已小有积蓄。“他们吃火车站,我们吃他们。”小倩不无得意。
“我们也是梅州人,老乡搞老乡,怎么好意思……”我们推脱。
“自己人有什么关系?自己人感情才好呢1。
我们谎称马上要去找朋友,请她们走。阿芹无奈,出门时,她笑着递来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呼机号码。已经出门了,她还在嚷:明天啊,明天我给你们找几个更漂亮的。
其实,在阿芹之前,另一个“士多”店的邻居——“胖女人”已经找过我们了。每次经过隔壁“士多”,她都会扯住我们,无论我们说话多么不客气。
3日晚9时,胖女人来缠我们。
当时我们回出租屋,胖女人恰巧看见。她坐在一张凳子上,一手摸着脚丫子,一手拎着矿泉水。夜色里,三十多岁的她显得很老,只有一双贼溜溜的眼珠在动。
“做‘生意’吧!邻居,优惠你们。”胖女人声儿大得像放炮。
我们决定去探探她的淫窝。
她领我们到了10米远的6号,可着喉咙喊:小妹,下来。
一个小妹噔噔噔下了楼,打开防盗门。
“听说现在查得严,这里又对着大街,安不安全?”我们试探。
“楼上就住着保安,你说安不安全?保证没人来查。我们和保安是有关系的,我做了几年‘生意’,从没被查过。”
我们不作声。胖女人强行推我们上二楼。
这是一间怎样邋遢的出租屋啊:不通风,灯光幽暗,床头还放着一个放卫生纸的大马桶。小妹说她还未满18岁,外省人,在四姊妹中排行老大,去年来广州,想挣钱养家。“靠身子吃饭呗,生意还不错,火车站那帮‘混混’都喜欢来这,近嘛。”
“屋子太孝太热了。”我们说。
“胡扯!附近有个出租屋,一屋住了十多个小姐,男男女女在屋里走动根本不穿衣服。”胖女人有些愠怒:你们到底做不做?别耽误事。要不是看在邻居的份上,我找人收拾你们。
我们迅速离开。
……
经过整整一周的暗访,我们发现三元里村的发廊的确少了,但不少“士多”却成了色情“中转站”。仅仅在世康大街,就有五家之多;在抗英大街,也至少有三家。
至于三元里究竟有多少在“士多”拉客的“阿芹”?又有多少在出租屋做生意的“小倩”?
我们不知道。
远景村很校
但这里却藏着一个颇具规模的“人肉市场”,在光天化日之下!
远景村位于广花三路东面,与毗邻的棠下、棠溪、沙涌等村形成一个庞大的出租屋群。这里距离广州火车站仅有几公里,在火车站出没的各路人马,几乎都在这一带落脚。
第一次踏进远景村,是中午1时,一天之中阳光最灿烂的时候。
地面污水横流,老鼠乱窜;空中尘土飞扬,棚架乱搭。扑面而来的是发霉、暧昧、近乎死亡的气息。
在三官后街,倚在每户楼房门前的,是一个接一个的卖笑女子。无一例外,她们的身体大面积裸露着,面上腻脂肥粉,眼睛斜斜的吊吊的,见着一人走来,总捏着嗲里嗲气的腔调:“靓仔,陪小妹玩玩啦!50块,想干嘛就干嘛1我们在巷里走过,女子们立即汹汹地合围过来:拉手、揽颈、扯衣、笑骂……我们好说歹说冲出她们的拦截,把一堆怪笑抛在了脑后。在巷口往里望,可以看到十多名女子分两边一字排开,好似在等待检阅。远景村内道路纵横交错,几乎每条小巷都有这样一排候客女,总数有几十人之多。
在巷口的“士多”、楼房门前台阶上,另坐着看似无所事事的赤膊大汉,叼烟,斜眼,阴沉沉地死盯你。一俟暗娼和嫖客稍有争拗,他们就上场了,问这问那,推推搡搡。从旁经过,我们心里不禁发紧。
在一家“士多”门口,几名女子和两个男人正讲价。他们目无旁物,大声地调情谑笑。“士多”老板和蹲在一边的闲人们趁势推波助澜:“你看小姐身材多好,哎呀,都是老乡,服务一下嘛。”一个男人眼见着顶不住了,同意交易,搂着小姐上了楼。
我们一直站在一边看热闹,结果引起怀疑。一个中年女人对一个大胖子耳语几句,大胖子便摇摇晃晃地朝我们踱了过来,屁股后面另跟着几个。他们个个把手揣在兜里,好像在掏什么,大胖子还故意咳嗽了两声。暴露了!我们顿时紧张起来。
眼看胖子越踱越近,凶寒的目光、粗大的臂膀触手可及。我突然大笑,对着面前的“士多”老板摇摇头,正告他:“货色太差!这都好意思出来做生意。”老板一愣,随之释然,尴尬地笑笑:“嘿,便宜,便宜。”我转过头对走过来的胖子说:“你有没有好一点的?”胖子也怔了一下,说:“这个,没有。”我们趁机大摇其头,一副十分失望的样子,慢慢逃开。
在另一条小巷,三个穿着绿色制服,戴着“执勤”袖章的治保员在“小姐们”身边走过,他们互相挤了下眼睛,笑着点头打起招呼来!
为了偷拍方便,摄影记者邓勃用一个小相机袋装着傻瓜相机,在贴着镜头处挖了个圆洞,绑在腰间,又在腰里缚了件衣服,一有需要就偷偷撩起衣服,用傻瓜机偷拍。虽然做得隐蔽,但仍是险象环生。
这天,我们又在村里“闲逛”。一栋房子的门前,两女人向我们抛来了媚眼:“玩玩啦。”邓勃撩起衣服,咔嚓咔嚓几张。不料,其中一个女的站累了,蹲了下来,她扭过头,视线刚好对着邓勃的照相机镜头!她盯着镜头看了两秒,突然惊叫一声,转身拉开门就往楼上走,嘴里大叫大嚷。蹲在一旁的几个打手,闻声站了起来。被发现了,赶快撤!我们撒腿就跑!
一溜烟,我们跑到大街上。外面虽有大片大片的阳光,惶恐仍像块湿布紧裹着身躯。
别走,拿“货”的马上就来
按照“道友”们介绍的常用找“货”(海洛因)的方法,3日下午,记者在走马岗一处天桥下问一名搭客摩托仔:“我们的瘾发了,哪里能买到白粉?”搭客仔很识趣地笑了,说:“十元车钱,我带你们去找啦。”记者问:“多少钱一克?会不会有假?”搭客仔说:“那要看你买什么样的货,一般纯的要三四百元一克,掺了假的50、80、100多的都有。”
几分钟后,他把记者载到广花一路某号一家挂牌为“西北风味小食店”、实为邪士多”的门口,先过去跟守店的一个三四十岁的外省妇女说了几句,过来叫我们拿50元给老板娘……
6日中午,记者又来到此处,一名外省人迎上来接洽。我们提出要买两克50元一小包的。此人走到牌坊东边20几米远的一家“士多”,去拿我们要的货。这时我们稍稍移动了一下站立的地方,更靠近马路,以便有不测时可脱身,马上就有一名胖胖的、五十来岁的外省人过来说:“你们别走,拿货的马上就过来了。”但我们还是想办法摆脱了毒贩的纠缠。
据村里的知情人说,这些出头露面的外省人,多半是身无技能的流浪汉,居无定所,常常露宿街头,平时还全靠老乡的“提携”,帮人推销点“货”提点成过日子。他们是这群毒贩结构中的“社会底层”。真正的大老板是很少与外人、生人接触的。
徘徊在瘾君子票贩子之间
“三条七”常从梦中惊醒,周身冷汗。他实在担心自己的毒瘾会传给即将出世的孩子。黑洞洞的出租屋里,他摸索着给妻子磕头,一个,又一个……
五天前,“三条七”在出租屋给我们说这些时,一阵呜咽。妻子一旁劝他:我们回老家,再不住这儿了——“三条七”就是在这里堕落成了“4号客(4号海洛因的吸食者)”的。劝着劝着,妻子也哭了。
“三条七”夫妇是广东陆丰人,从小就住同一条巷,同读一个班。1997年底,“三条七”一退伍就结了婚。1998年仲夏,“三条七”独自下广州,在距火车站不远的棠下村租房住下。“白天在站西路卖服装,晚上在出租屋想老婆,爽”。
事情来得很意外——
去年春节,“三条七”总看见自己摊儿后头蹲着个“大胡子”,卷个纸筒在吸,很陶醉的样子。他很好奇,心里痒痒的。元宵那天,“大胡子”让他也来一口。“三条七”一愣,旋即凑过去吸了一口。因为吸得太急,他被呛得连打几个喷嚏。稍后,他觉得头晕,但很舒服。“我知道我吸上毒了。”
“三条七”结束了从前。
他开始和毒品打得火热,每天都在出租屋吸食。摆摊赚来的钱,很快都化作缕缕青烟。他毒瘾越来越大,吸食还不过瘾,又改用针管注射。
出租屋成为“三条七”吸毒的温床。他丢了身份证,也没办暂住证,愣是在出租屋住了下来,在此吸毒也从未有人过问。而在出租屋附近的三元里村,只要随便在那里晃一圈,保准有人过来搭讪,并很快塞过来一个小纸包。“买毒品都是在大白天、大街上,根本不像大家想的那样偷偷摸摸。”
“三条七”每况愈下,进货的老本也吸进了肚,服装摊摆不成了。去年的8月热辣辣,他躺在出租屋里,想钱,想赚钱,想赚钱吸毒。
他只好去火车站炒票,他听说炒票来钱快。两天下来,他只赚了一身臭汗。出租屋空荡荡,他哭得山响。
知夫莫若妻。妻子很快来到广州,也很快明白了这一切:丈夫大热天还穿着长袖,两颗门牙已经烂掉,才27岁已淡了性趣,总蹲在墙根下———全世界的“4号客”都喜欢蹲姿。
妻子只好帮他去炒票。妻子成了他的信用卡。“三条七”没本钱,就让想买票的旅客先拿出来,旅客不同意,他就拿妻子作抵押:你看她怀着孕,跑得掉吗?其实,“三条七”从内部根本拿不到票,他只是往买票长龙中插队。如果别人不让插,他会指指妻子:“你看我老婆挺着个大肚子,帮个忙吧。”
一张票赚二十,一天赚百八十块,可“三条七”过得还是苦。要知道,他每天要花60-100元买毒品埃他这样描述自己的一天:上午10时离开出租屋,步行到三元里村买三包毒品,再折回出租屋,躲在厕所里注射一针;约摸11点钟,坐公交车到火车站炒票,下午3时返回出租屋,再注射一针;下午4时又从出租屋赶到火车站,炒票至晚上9时,回出租屋注射最后一针。
对“三条七”的吸毒,妻子没有太多指责。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她震惊了:一是“三条七”用不洁针管注射毒品,引起屁股感染,被开刀生生挖掉一块肉;二是“三条七”有时瘾来了,连自己的尿也回收注射。
她求他:戒了吧。
“三条七”把门反锁,躺在阁楼里。八小时后,他开始打哈欠流鼻涕,“就像有几万条虫子在骨头里咬。”他拿头撞墙,扯头发抓胸脯……30个小时后,“三条七”还是跑向了三元里村。
几天前,“三条七”又去求一个老刑警:“我在这风头上再去火车站炒票,你把我当场拿下,拘留我半个月,让我戒了,然后我回老家———再过个把月,我老婆就要生了。”
标签:人肉市场,附图,揭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