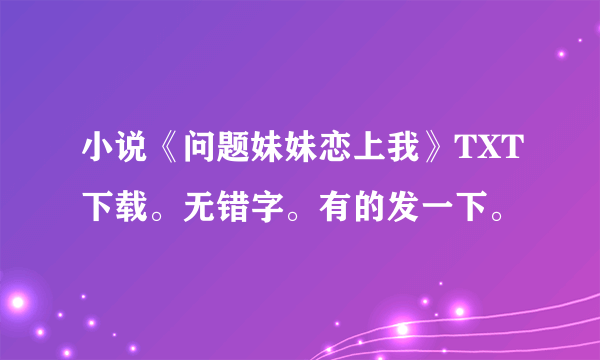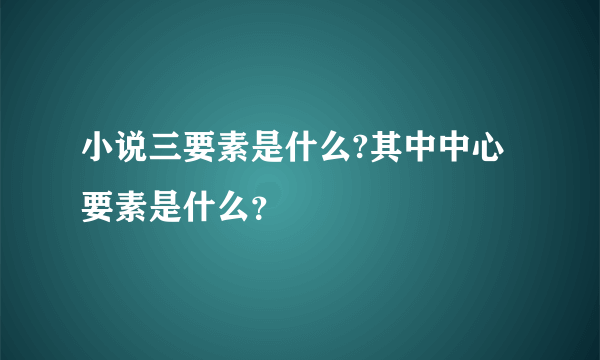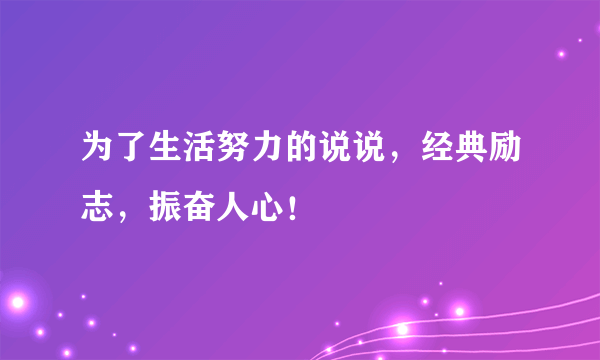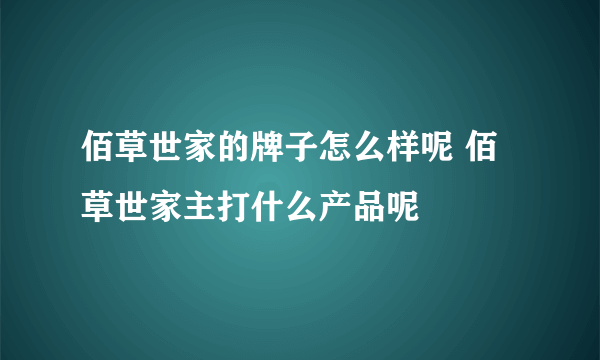近年来,帕慕克一年里一半时间在土耳其,一半时间在美国,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比较文学。平日不上课时,他去图书馆,逛书店,更经常去博物馆,对闭馆时间谙熟于心。他住在哥大附近面向哈德逊河的公寓里,客厅宽敞,有三扇窗户向阳,一张大书桌,在木地板中心,像一只船,浮在金色湖面上。他目光敏锐,声音洪亮,说英语时带口音,有土耳其语的影子。
帕慕克的书架
新作《红发女人》里,少年杰姆跟随挖井人马哈茂德在恩格然小镇挖井。师徒在劳作中逐渐亲如父子,但水迟迟不来,失望的杰姆与流浪剧团的红发女人越走越近。一次猝不及防的意外后,杰姆仓惶逃离小镇。三十年后,成为建筑公司老板的杰姆在机缘巧合下重回当年的小镇,迎来属于自己的命运。和帕慕克的生活一样,他的作品继续在东西世界间摆渡,以他钟爱的方式对两种文学传统进行比较。他坦言现在自己写得很慢,每一部作品都是在胸中酝酿已久。在完成《红发女人》后,他立刻开始了下一部作品的写作。
帕慕克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系列收藏
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,世纪文景发布的出版计划中,就包括《红发女人》中文版,小说即将在3月出版。近日,在帕慕克的纽约住所进行了专访。
奥尔罕·帕慕克
您初来美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是什么?
帕慕克:好问题。我是1985年和我前妻一起来的,接触到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电影院等各种资源。那是电子革命的前夜,我来自视野相对狭隘的土耳其,它的文化产业很小,突然间,我接触到这个巨大的文化资源,尤其是美国高校、文化组织、电影等。当时电影非常重要,而且也很难获取。那年我33岁,在土耳其已是知名作家。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化冲击促使我询问自己:我的土耳其身份是什么?什么是“土耳其特质”?当时我已经写了两部小说,但我对苏菲派、穆斯林文化及文本都不太感兴趣;我在政治上是一个亲西方的自由人士,我更多的是向欧洲寻求先例。当我第一次来纽约、经历那场文化冲击后,我开始阅读更多经典的土耳其文学、奥托曼文学,或许我开始对自己说:我的老天,世界文学这么丰富,美国文学这么丰富,土耳其文学在什么位置?我开始为此忧心。
当时我很幸运,哥伦比亚大学有人读到我的小说,他们聘请我做访问学者。哥大有很多优秀的土耳其藏书,奥斯曼帝国时期著作。我阅读了这些书,并完成了小说《黑书》。文化冲击帮助我重访作为土耳其人的根,但重访方式并不是老派传统的,而是后现代、实验的。1985年,后现代主义在这里非常重要,我从中学到很多。我称自己为后现代派小说家,很多人不愿被冠上这样的称号,但我并不为此尴尬。它拯救了我。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帮助下,在博尔赫斯、卡尔维诺的启发下,我以一种全新的、当代的方式讲述奥斯曼故事。这是我的文学的根基。
当您经历文化冲突时,是否也会对这种文化进行批判?
帕慕克:进行文化批判很容易。我在文化身上寻求的不是它失败之处,而是我可以从中汲取、用来表达自我的东西。打个比方,我收藏了很多中国山水画,为什么?我在写《我的名字是红》时,我对印度画和中国画产生了兴趣,于是读了很多相关著作。对我来说,它们是很好的资源。但我并不是中国画专家,也不是后现代文学的专家。我了解它们,向其借用。文化对我来说像树,结了可口的果实,供你采摘,加以使用。每个文化都有弱点,有无聊的地方。但当我对它不感兴趣时,我会想,或许是我自己对它缺乏了解。我批判政府,但对文化态度更温和。在纽约时,我的女友、家人、朋友都不在身边,我常去博物馆。每年在纽约教一学期的书对我来说很重要,它让我得以脱身祖国糟糕的政治环境。
《巴黎评论》的采访里,您曾提到“每本作品都代表了作家的一个发展阶段”,这本新书的创作过程中,您感受到了怎样的发展或变化?
帕慕克:这本小说和我其他作品相比,是一部更简单的、节奏更快、也更短的小说。这是我自己设定的长度。它仍然囊括了我在《我的名字是红》、《黑书》及其他作品里探索的主题,对古典故事进行改写。但在这本书里,我第一次比较了索福克勒斯的《俄狄浦斯王》和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的《列王纪》,它们都是企鹅出版的经典作品。我在哥伦比亚教书,索福克勒斯的名字就刻在哥大巴特勒图书馆的墙上。这些欧洲的、西方的经典让弗洛伊德得出了弑父说。但在土耳其,我们有父亲弑子的故事,它蕴含了不同的意义,因此我想讨论这些主题。
随着年岁增长,我写作的速度渐渐不及我对下一部作品畅想的速度。而我在过去四十年里一直在设想新的作品,因此我有很多尚未完成的书,我常常谈起它们。现在,我的每一本书都是我思考了二十年、三十年的作品。在这段时间里,你会琢磨这个主题,检查它的可行性,探索它的问题和戏剧性。我还要忧心怎么去写,它美不美,我能否出色地创造我的人物?这些总是很难的。无论你是在写第一部作品,还是第十一部作品,都一样难。但足够的思考会有所帮助。
打个比方,这本书就来自两个灵感。1988年,我在家写作时,窗外不远处有一个挖井人带着他的学徒打井。下雨了,他们的帐篷不管用;平时,他们看电视,煮饭。他们给我讲了一个故事,但我花了二十五年才把它写出来。其二,我在写作《我的名字是红》时读了很多古典故事,就连土耳其人都忘了它们。我还在教索福克勒斯的《俄狄浦斯王》。在这些年里,这些故事彼此交织,融合在了一起。
还有一个原因,土耳其的政治局势正在恶化,越来越独裁。但不幸的是,人们还是会投票选当前政府,为什么?我给出一个略为夸张的回答:因为政府在为他们找水——给他们提供经济增长,为底层提供服务——而其他政党没法做到这一点。我强烈地认为土耳其人支持执政党,不是因为宗教或政治因素,而是因为经济发展。
《红发女人》
小说中的红发女人让人印象深刻,尤其是她面对天生红发的女人的质疑,说出“我是主动选择成为红发”时。
帕慕克:首先,这句话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。我对一个教授朋友说,我在写一本小说,关于一个红发女人的,而这个朋友认识一个红发女人,她告诉了我这个细节。但我还需要把这个细节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。听她讲了那个故事后,我对自己说:天哪!或许我应该给红发女人一个独白。另外,在世界各地,红发女人有不同的意义。这本书出版两个月后,我在英国,天,到处都是红发女人,而且她们都是天生红发。在英语文学里,从莎士比亚到普拉斯,红发女人都代表着愤怒的女人,无法驯服的女人。但在土耳其,红发是染出来的,是人工的。它代表对社会的挑战:“没错,我喜欢这样,我想要与众不同!尽管这是一个负面形象,但我仍然选择这样。”
这本书第一部分井下世界的描述非常动人,您是怎么为此做研究准备的?
帕慕克:我喜欢为每部作品做研究准备,但我并不以此自豪。要说让我自豪的话,还是我作品的文学性和匠心。当我告诉人们我做了多少准备,我觉得自己是个没有才华的人。写《雪》时,我去了东北边城实地体验;写《我的名字是红》时,我读了大量经典文献,查了很多画作;写《我脑袋里的怪东西》时,我采访了很多街头小贩。这本书首先来自我在二十五年前采访窗外那对挖井师徒,但那仅仅是个故事。那么挖井的技巧呢?三年半前,我决定写这本书,就从伊斯坦布尔找了许多退休的挖井人,采访他们。遗憾的是,我们没有挖井人的回忆录。但他们的故事精彩极了!我找到的这些挖井人,因其技艺出众,被政府雇去挖掘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深井,拜占庭教堂的古井,他们在井下找到了钱币、武器、各种骨头。这些素材也让我渴望把故事写出来。
关于书中主人公的儿子有一个细节,是他在为宗教文学期刊撰稿。这是你有意识安排的细节吗?
帕慕克:是的。相对普通土耳其人来说,我是一个亲西方的、自由派人士,我的价值观更偏世俗。但这不意味着我的人物也应都和我一样。过去的土耳其世俗作家写社会小说,但他们避开土耳其人的宗教不谈,这是有原因的,因为他们不想过分强调它。但事实上,你必须准确地呈现你的人物。现在土耳其年轻一代里有伊斯兰信徒。很多诗人就对此感兴趣。在《雪》里,我也塑造了一个伊斯兰信徒,他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诗人。土耳其有很多诗歌杂志。我逛街时会买奇怪的杂志,并想象什么样的人在写这些东西。好奇心、研究、想象、观察、思考。这些也是我的工作。我喜欢作家这个职业,它让我像一个人类学家、历史学家、社会学家一样生活工作。我的虚构也基于对其他生命的想象。
正如哥大文学教授亚当·基尔希提及,小说中弑父与弑子两大文学传统并列,让第二部分的结尾富有悬疑性。
帕慕克:是的,的确如此!让读者能了解这两大神话是很有趣的,这本小说是个后现代故事,让古老的神话进入现代故事,让读者询问:是父亲杀了儿子,还是儿子杀了父亲?这正是阅读这本书的方法。这是一本小书,一本关乎理念的书。
至于故事最后的结局,你不能光从情节来归纳。这本小说有时是一个寓言体小说,但又不完全是一个传统中世纪寓言。对我来说,它传达的信息并不来自它的情节,而是这本书试图理解和同情什么。当我写作时,我与众多人物都产生了共鸣:有时是父亲,有时是孩子。但更重要的是,谁对谁错并不重要。我更关注的是他们各自如何看待这个世界。我们写小说主要是为了两个原因:其一,表达自己。我如何看待这个世界,我的观念,我面对所见所闻产生的感慨和情绪。其二,去理解和我不同的人,从他们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,这很有趣。体验不同的视角是阅读至高的乐趣之一。我对写小说的本质有这样一个总结:写自己时,要让读者以为你在写别人;写别人时,要让读者以为你在写自己。
也有可能是为了生存。
标签:帕慕克写,小说,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