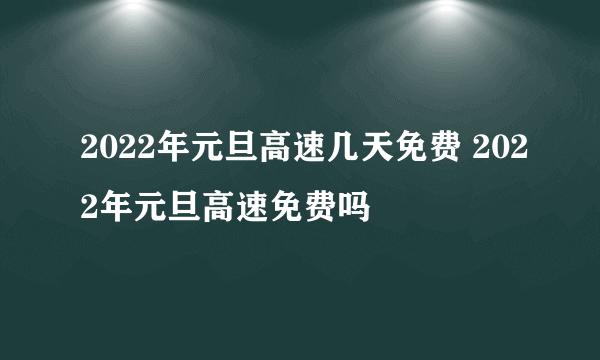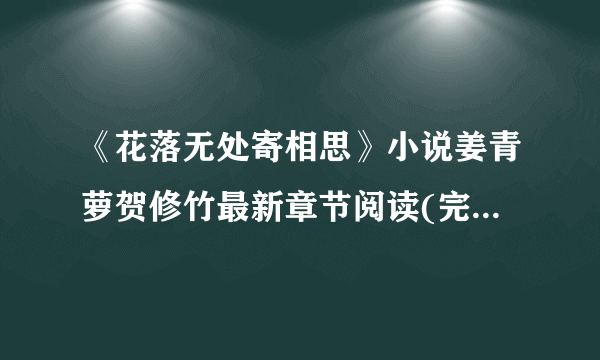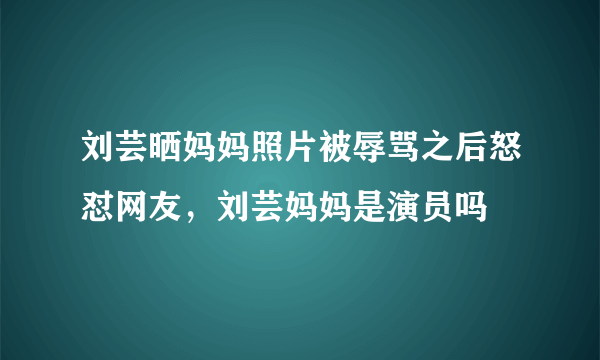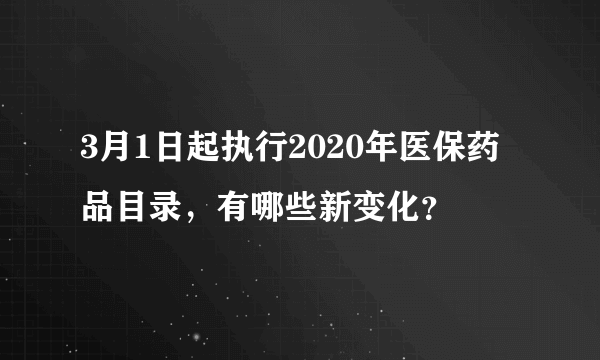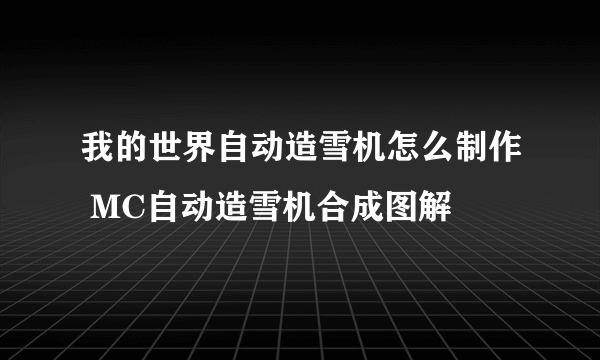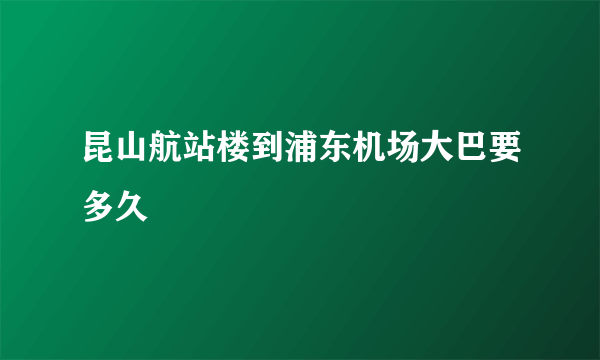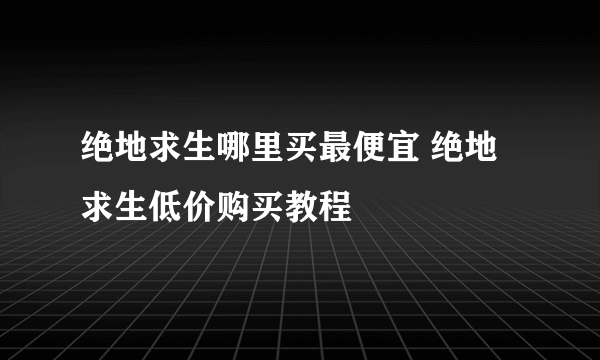十虐
一虐美人迟暮
明锐东忙,非常忙,忙到两个孩子几乎见不到他的影子。关于明锐东的一切,他们只能从报纸上看到。比如父亲上个月出了国去了法国,从巴黎给明楼带了一套画具,明楼宝贝的不行。又比如前几天父亲又去了苏州,苏州老家的马场。
明家祖上是靠马起家的,发达后的明家人,代代都是马上好手,明镜明楼二人也不例外。明楼还小的时候,明镜就总求着父亲带她去苏州玩。
“玩?女孩子家,骑马做什么?失了风度。”
明镜从小就是倔脾气。
“明家儿女,不会骑马,又算个什么?”
明锐东反驳不了,只好依着她。明镜也是骨子里带着的天赋,骑起马来不输很多御马多年的人。明锐东看的也不知是高兴还是不高兴。后来明楼从小豆丁长成了豆芽菜,明锐东更忙了些,也就没有这个精力管这些小事,便任由他们玩着了。
“姐姐,唱歌给我听好不好?”
“明楼想听什么?”
“姐姐唱的什么都好。”
“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…”
那时候弘一法师刚刚皈依佛门,留下的歌谣传唱一时,姐弟二人还不懂歌词含义,只当旋律好听。晚上明楼躲在明镜怀里睡觉时候,明镜就轻轻拍着被子,被子里卷着的小明楼呼吸在歌声中渐渐平稳,明镜看小明楼睡着了,也就抵不住困意,睡着的前一秒还不忘把小明楼圈进怀里。明镜那时候还是少女的嗓音,带着些柔嫩质朴,唱腔不是歌伶的婉转也不是洋人的生硬。地地道道的带着上海口音的中国话,唱出来格外有韵味。小明楼伴着歌声入睡,整夜整夜的梦里,都是这仙丹一般的歌声。
“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…”
明家产业越做越大,明锐东弥补般在上海也开了个马场,马场在近郊,周围种了他喜欢的柳树。而这马场除了那些有名的暴发户外,明镜便是最忠诚的客人。明楼长大了便喜静,除了汪曼春有时会缠着他出去,他便和明诚两人整日整夜的待在书房里写写画画,明镜也不计较,得了空就往马场跑。她最喜欢一匹雪白雪白的马,她叫他“月下”。
马夫们只在暗地里嘲笑,花前月下,花前月下,她明镜装什么巾帼,到底也只是个儿女情长的金枝玉叶。
“月下飞天镜,云生结海楼。是个好名字。”一个年轻人跟在明锐东身后半米的距离,声音朗朗,行动带风。
“镜儿,这是于家公子,于亭。”
“大小姐。”
“旁人只道花前月下,你倒是与他们不同。”
“明家大小姐明镜,在我眼中从来都不是绣花枕头般的人儿。”于公子脸上是温润的笑意,一句烂俗的赞美从他嘴里说出竟让人生不出讨厌。
“还算识相。”明镜脸上没什么表情,心里却暗暗的开始开心着。
“我这有匹好马,精挑细选百里挑一。牵来送给
明先生。”于亭牵了一匹马走过来,男人长得英挺,配着旁边高大威猛的骏马,让人移不开眼睛。
一匹好马,大抵就是这样了。通体如墨碳般黑油油的发亮,只有四只马蹄是雪白的颜色,鬃毛威风的跟着头甩动,四蹄踏地,地上的灰尘扬起来几乎迷了明镜的眼。
威风凛凛。
明镜甚至想不出别的词来形容这匹马。她把他改名云生,与月下相配。云生和月下很快有了后代,明镜看着开心,想着自家马场里又会多了好多逸尘断鞍的好马。
“于先生”
“于亭就好。”
“悲欢聚散一杯酒”
“南北东西万里城”
长身玉立的男子温和的向女子笑,那女子身形细瘦,个子很高,几乎能和高大的男子平视。二人站在夕阳下,这正是春末夏初小麦喝饱雨水的时候,晚风轻轻柔柔的从柳叶间穿过,又飞过于亭肩头擦过明镜发间,二人身上都满是属于马场的青草气息。斜阳渐矮,暖金色的夕阳把两个影子拉长,再拉长,薄暮的光斜斜的打在明镜年轻的脸上,把她的脸颊映的棱角分明,就像刀凿斧刻的雕塑上笼罩了一层轻纱。她本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沪上柔静的女子,容貌性格,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巾帼的侠气。于亭看着明镜挺秀的侧脸,不知不觉呆了。明镜的余光捕捉到他如同定格般的一幕,抬眼对他一笑,高大的男人脸上满是被发现的局促。明镜眸子里笑意更浓,拉过男人的手握紧。掌中的手细瘦削长,干净有力,二人的手心紧紧贴在一起。温度穿过皮肤表层一丝丝的经过每一个神经末梢,缓慢有力的流到两人心里。
男人低沉的嗓音轻轻哼起了婉转的小调,女子轻柔的声音附和。
“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…”
“晚风拂柳笛声残,夕阳山外山…”
“天之涯,地之角,知交半零落…”
“一壶浊酒尽馀欢,今宵别梦寒…”
这一刻,夕阳是他们的,云层是他们的,晚风拂柳,西风残照都是他们的。他们在对方的掌心里,看到了全世界,看到了自己。
日子缓慢优雅的流着,明镜放学了就去马场,亲手照料着云生和月下。于亭也每天都来,二人经常会“偶然”遇到。连明诚都察觉到明镜脸上越来越浓的笑意。
因为明镜高兴着呀,高兴着明家马场的利润节节攀升,高兴着自己又考了个第一名,高兴着明楼明诚两兄弟的感情越来越好了。
还高兴着什么呢?
比如云生和月下有了宝宝,两匹马的感情好得不行,如胶似漆。
比如于公子天天都往明家跑,也不知道是做些什么。明锐东偶然撞见,也不见外,没了刻板的礼没了世家的架子,只剩下长辈的宠溺和疼爱。
比如明镜总是能收到一封窄窄的信,信间漫不经心的藏着一片花瓣,一枚树叶又或者简简单单的一张简笔画。
只是这画的内容单一的很,没别的,一对玉镯。画这对镯子的人总是变了各种角度描绘着,光线,明暗,角度,位置。前前后后明镜不知道收到了多少张画着镯子的纸,她都小心翼翼的藏着,精心的挑了个苏绣软锦盒子,把画一张一张的存着。
明家和于家结亲,轰动了整个上海。连平头百姓都津津乐道,上海两大世家结亲,怕是将来的整个上海滩都要被明于两家平分了。
“何以至契阔,绕腕双跳脱。我要带你去马场,我们的马场。你和我,云生和月下,我们去看夕阳背面的大海,我会在海边给你带上这双镯子。”
第二天,明锐东遇刺身亡。
明镜才十七岁,明楼还在上中学,明家摇摇欲坠。整个上海的人都是说不出的惋惜,惋惜偌大一个明家,就这样随着明锐东的死去而死去了。
可明镜不信,她要强,甚至有些要强的过分。
“明镜,你可知道什么是奉道?”
“一生,不嫁娶,不传艺,不留后。”
“你当真想好了?”
“请大师成全。”
是明镜退的婚。她穿一身黑色素缟,面色虽憔悴但有神,妆容虽浅淡但精致,她不允许自己失了任何风度,无论什么时候。她还回了那些悉心保管的画纸,那些藏着花叶的信笺,最后,才脱下那双腕上那对清凌凌的玉镯。
她把这些一一交到于亭的手里,眼底毫无泪水,脸上也没有什么表情。她似乎把自己包裹在那层厚重的黑纱里,最后一起融为黑色,于亭指尖动了动,还是忍住了想要向她伸去的手。
“是我无缘于你,再无其他。”
她神色没有丝毫松动,融进了背景黑漆漆的夜色里。
“明镜…”
他手中的那对镯子被锦盒盖住了光芒。
应该戴在她腕上的,于亭这样想。应该戴在她腕上的。
“我奉道了。”
于亭垂首,张开嘴用力的呼吸着。
“…以后,怕是只能在办公室见到明董事长了吧”
于亭笑着,却甚至不敢抬头看对面的女子一眼。高大的男人,努力低下头掩饰眼底的泪水。他原本挺拔的身影,此刻却像蜷缩起来一样。明镜看着男人,双手交叠,白的泛惨的指尖握着自己的手腕。
“…我保证,明家和于氏,一荣俱荣。”
明家股票大跌,于氏受损更加严重。这场风波的最后,是于家公子携家眷出走上海,另谋生路。而明家,风雨飘摇,却岿然不动。
那年明镜十七岁,她扛起了整个明家。
现在明镜三十七岁,她想帮助整个国家。
她骨子里就存在着一种惨烈,飞蛾扑火,向死而生,从死路中谋求生路。
明家成了上海滩经济的顶梁柱,富极一方。
可明镜,从此再未戴过玉镯。
她突然想起,他们曾经合唱的那首歌。
“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。
晚风拂柳笛声残,夕阳山外山。
天之涯,地之角,知交半零落。
一壶浊酒尽馀欢,今宵别梦寒。”
弘一法师作词作曲,唤作《送别》。
明镜身子晃了一下,失声痛哭。
“求你…救救我…”
“小姑娘,姑娘!”
于亭救了个流落街头的小女孩,他实在不明白,这么小的孩子,这些病是从哪里来的呢。他不去细想也不敢细想,带着小女孩治好了病,收为义女。
“你可以叫我于老板,姑娘,你叫什么名字啊?”
“花名…锦瑟…”
于亭紧紧的锁了眉心,握紧了女孩纤细的小手。
“我收你为义女,以后,你就是于家人了。”
“于老板…”
“曼丽,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?”
于亭看着小女孩眼底发出的光,倔强挣扎的眼神,他晃了神。
十六七的年纪。
明镜和他订婚时的年纪。
二十年了啊。
最是人间留不住
朱颜辞镜花辞树
标签:美人迟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