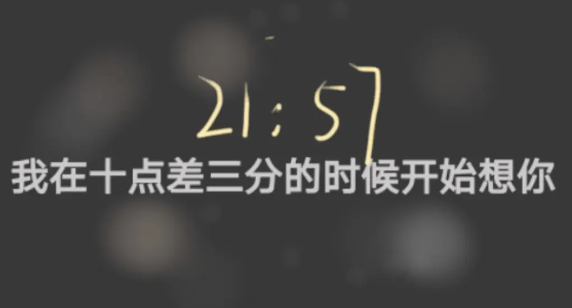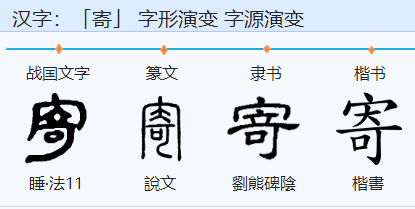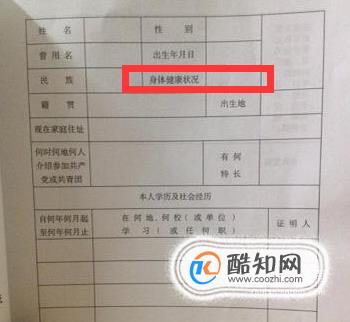“究天人之际,弊虚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的意思——想用它来研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关系,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,形成一家的学说。
1、究天人之际:
所谓“究天人之际”就是要探讨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。在这个问题上,司马迁继承了先秦以来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传统,他反对以天道干预人事,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,天是天,人是人,天属于自然现象,与人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。这种观点与汉武帝所提倡的儒学正宗的所谓 “天人感应”学说相对立。
2、通古今之变:
所谓“通古今之变”,就是要通过历史的发展演变,寻找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。这里涉及两种思想:
①历史进化思想: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表现的历史观与董仲舒“天不变,道亦不变”的观点不同。他认为历史是通过各种改革向前演进的。因此他对于历史上出现的政治改革,总是采取称赞的态度,如对战国时期吴起的改革,商鞅的变法促进历史前进的作用是有一定认识的。说吴起改革的政绩是“诸侯患楚之强”;商鞅变法的政绩是“行五年,秦人富强”,“行之十年,秦民大悦,道不拾遗,山无盗贼,家给人足,民勇于公战,怯于私斗,乡邑大治。”对秦始皇的问题也是如此,司马迁曾称“秦为暴秦”,“无道秦”,“虎狼之秦”,但对秦始皇实行改革的功绩还是肯定的,“秦取天下多暴,然世异变,成功大”。反映出一种厚今博古的租衫思想和一个历史家“通古今之变”的眼租型燃光。
②原始察终,见盛观衰的辩证思想:
所谓“原始察终,见盛观衰”,就是透过一些历史现象,来观察一个时代或一项具体制度由盛而衰之理。历史的盛衰都不是偶然的,都是有迹可寻的,而且往往“盛”中包含了“衰”的因素。如《平淮书》中记述武帝盛世太平,但孕育着衰败的因素——富贵者役财骄溢,争于奢侈,“物盛而衰,固其变也”。说明司马迁在研究历史时,注意历史事实的因果关系,注意说明历史的转化,带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。
3、成一家之言:
所谓“成一家之言”,就是借写这样一部历史著作,来表达他的某些独到的历史见解,表达他的某些社会、政治思想。《太史公自序》中说他的理想是使《史记》成为《春秋》第二,他自己成为第二个孔子。当时人们普遍这样认为,孔子“因史记(鲁史)作《春秋》,以当王法”,这部王法“记天下之得失,而见其所以然之故,甚幽而明,无传而著”,它“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。”孔子之所以借历史来寄寓理想,是因为孔子说过:“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。”司马迁写《史记》,窃比《春秋》,也是寄寓理想于其中的,而他的理想也是靠历史事实的叙述来体现的。
【作品出处】
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出自《报任安书》(也叫《报任少卿书》),是西汉史学家、文学家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。司马迁以激愤的心情,陈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,抒发了内心的痛苦,说明因为《史记》未完,他决心放下个人得失,相比“死节”之士,体现出一种进步的生死观。行文大量运用典故,用排比的句式一气呵成,对偶、引用、夸张的修辞手法穿插其中,气势宏伟。这篇文章对后世了解司马迁的生活,理解他的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【创作背景】
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,字少卿,早年在大将军卫青门下。当霍去病渐渐受到汉武帝的宠信,逐渐凌驾在卫青之上的时候,卫青的故人、门下都投靠霍去病了,并因而获得官爵,只有任安不肯,仍效命于卫青。
在巫蛊之祸中,任安担任护北军使者,握有兵权,戾太子派人持节到他那里要求发兵助战,他受了节,但仍闭城门,不肯接应太子。
事件平息后,汉武帝赏赐了那些系捕太子的人,而把那些跟随太子和为太子助战的人都治以重罪。关于任安,汉武帝对他的做法认为还可以,没有责怪他。可是后来有人进言,说太子在“进则不得见上,退则困于乱臣”的情形下,不得已而“子盗父兵”,其实并无造反之心,使汉武帝感悟到太子是冤枉的。于是,先前所做的处置,又重新检讨,变成了与太子战、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。而当汉武帝心理转变的时候,便对任安对待太子的态度产生了根本的怀疑,他怪任安不帮太子,却坐持两端,准备看谁胜了就依附谁,于是就判他腰斩。
任安自认为自己是冤枉的,十二月就要行刑了,他写信给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司马迁,请他设法援救。
司马迁接到这封信时,他的心里相当为难。他了解汉武帝,自己就曾尝过汉武帝暴怒之下的痛苦,他实在不愿意再遭到第二个“李陵之祸”。论交情,李陵与他“素非相善”,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,双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。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为太子报仇,任安的死判,觉无平反的可能。他要把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,向老朋友说明,并请求他原谅。于是,在征和二年十一月,五十五岁的司马迁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安。
任安终于被腰斩了,司马迁也在感叹中度完了他的余生。前有李少卿(李陵),后有任少卿(任安),都在他生命中激起很大的涟漪。显然前者是狂风暴雨式的,而后者只是前者的余波,它看起来平静而又清澈见底,却又让人沉思。
【作品原文】
古者富贵而名摩灭,不可胜记,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。盖西伯(文王)拘而演《周易》;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《兵法》修列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,故述往事、思来者。乃如左丘无目,孙子断足,终不可用,退而论书策,以舒其愤,思垂空文以自见。
仆窃不逊,近自托于无能之辞,网罗天下放失旧闻,略考其行事,综其终始,稽其成败兴坏之理,上计轩辕,下至于兹,为十表,本纪十二,书八章,世家三十,列传七十,凡百三十篇。亦欲以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。草创未就,会遭此祸,惜其不成,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。仆诚已著此书,藏之名山,传之其人,通邑大都,则仆偿前辱之责,虽万被戮,岂有悔哉?然此可为智者道,难为俗人言也!
且负下未易居,上流多谤议。仆以口语遇遭此祸,重为乡党戮笑,以污辱先人,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?虽累百世,垢弥甚耳!是以肠一日而九回,居则忽忽若有所亡,出则不知其所往。每念斯耻,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!身直为闺閤之臣,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!故且从俗浮沉,与时俯仰,以通其狂惑。今少卿乃教之以推贤进士,无乃与仆私心剌谬乎?今虽欲自雕瑑,曼辞以自饰,无益于俗,不信,适足取辱耳。要之,死日然后是非乃定。书不能尽意,略陈固陋。谨再拜。
【作品赏析】
这篇文章是司马迁在自己生命遭受极端摧残之后写的。
“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,用之所趋异也。”司马迁认识到生与死的价值,并作出了毫不含糊的解释。这种人生观发扬了孟子“生”与“义”的精神之髓,并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。作者从生命历程与创作的关系上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,就是“愤怒出诗人”的文学创作规律。他在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中写道:“屈平正道直行,竭忠尽智以事其君,谗人间之,可谓穷矣。信而见疑,忠而被谤,能无怨乎?屈原之作《离骚》,盖自怨生也。其志洁,故其称物芳。其行廉,故死而不容。自疏濯淖污泥之中,蝉蜕于浊秽,以浮游尘埃之外,不获世之滋垢,嚼然泥而不滓者也。推此志也,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”司马迁用诗一般的语言,高度评价屈原的一生,是写屈原,也是在写自己。“盖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;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……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这些话体现了作者对统治者有清醒的认识,看透了这个社会。
司马迁是叙事的高手,《报任安书》这篇作品把事件叙述得凄婉动人。“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,深践戎马之地,足历王庭,垂饵虎口,横挑强胡,仰亿万之师,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,所杀过当。虏救死扶伤不给,旃裘之君长咸震怖。乃悉征其左右贤王,举引弓之民,一国共攻而围之。转斗千里,矢尽道穷,救兵不至,士卒死伤如积,然陵一呼劳军,士无不起躬流涕,沫血饮泣,张空弮,冒白刃,北向争死敌者。”这段叙述,激烈悲壮。叙述是抒情的基础,情生于事,叙事以抒情;事随情陈,写情以染事。本文把叙事和抒情融合在一起,“是以肠一日而九回,居则忽忽若有所亡,出则不知其所往。每念斯耻,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!”这既是叙述又是抒情,如怨如慕,如泣如诉。
本文是书信体。书信最适合任意挥洒,不受羁绊。在信中,司马迁借任安要求其“推贤进士为务”,陈述了自己不能听从的理由,由此引发了一大篇愤激之词。他写了自己所受到的冤枉,虽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是受冤的,但处处暗含着怨怼之气,表现了作者骨子里不认为有罪的倔强性格。本文写了自己对人生价值的探索,点明了中华仁人志士生死观的内核。本文写了作者身残志坚的英雄气概,在耻辱中写完了煌煌巨著《史记》。本文写了世态炎凉,人情冷暖。“家贫,货赂不足以自赎;交游莫救,左右亲近不为一言。身非木石,独与法吏为伍,深幽囹圄之中,谁可告诉者?”既有对世态的感叹,也有对任安的委婉责备,都通过书信的形式,向朋友道来,激越雄壮,如江海波涛,汹涌澎湃。
本文所表现出来的超越时代局限的历史穿透力令人感佩不已。作者对汉武帝的态度是很明确的,全文无一处盛赞之语,处处是怨尤愤懑。“未能尽明,明主不晓”;“拳拳之忠,终不能自列,因为诬上,卒从吏议”;“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,文史星历,近乎卜祝之间,固主上所戏弄,倡优所畜,流俗之所轻也”。这些语言实际是对汉武帝的控诉。作者写《史记》不是为帝王树碑立传,也不是为将相歌功颂德,而是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。作者希望“藏之名山,传之其人,通邑大都,则仆偿前辱之责,虽万被戮,岂有悔哉!”
【作者简介】
司马迁(公元前145年-公元前90年),字子长,夏阳(今陕西韩城南)人,一说龙门(今山西河津)人。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。司马谈之子,任太史令,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,后任中书令。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,被后世尊称为史迁、太史公、历史之父。
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、董仲舒,漫游各地,了解风俗,采集传闻。初任郎中,奉使西南。元封三年(前108年)任太史令,继承父业,著述历史。他以其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《史记》(原名《太史公书》)。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,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,到汉武帝元狩元年,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,为“二十六史”之首,被鲁迅誉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。
标签:通古今,一家之言,之变